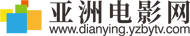2023-03-14 15:00:47 来源:北京晚报
本版风景均为阿拉·古勒所摄
2023年2月6日18时24分。我从寓居的东北之城旅行到北京,夜间在入住的京伦酒店1023的客房看到远方灾难降临的消息。7.8级的土耳其大地震带给我心头的震撼,这个国家作为整体生长在心里,某座城市的震荡如同整个国家的摇撼。我的记忆之镜映现出博斯普鲁斯海岸,祈愿那里安好。人类所经历的灾难中,地震应该是最为恐怖的。当然,没有灾难不恐怖,然而大地震造成的灾难比飓风持久,比海啸广大。震感强烈的地震造成的毁灭深远辽阔,它显示出浩劫的残酷性。大地震荡时,身处震中的人们无可逃遁,瞬间袭来的强烈摇撼,使楼群粉碎,山体崩塌,河流满溢,公路断裂,生命遭受重创,挤压在破碎的建筑物里的死亡,遗落在瓦砾废墟中的人的伤残肢体显示出尘世至哀的景象,而活着的人在尘土飞扬中仓皇脆弱如受惊的蚁群。孤独和绝望,大地震在毁灭人类的物质性家园,同时也带给人精神重创——你知道在浩劫中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
事实上,此次地震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震中位于北纬38.00度,东经37.15度。(此刻地震造成的遇难者已达41000人)。因为有过土耳其的旅行,地震的消息自然牵动着心神。我察看震中所在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地震带。在地震现场的人们拍摄的短视频经由互联网流传出来,你可以零距离地看见灾难发生的实况。此刻人类刚从瘟疫中喘息,强烈地震又将悲剧降临。我能想象它浩大的灾难现场,奔赴震灾现场的有救援者,自然也有媒介工作者。在地震发生之始,我就看见微信有朋友即时直播震灾现场的消息。他们冒着余震的危险,踏着瓦砾废墟,寻找幸存下来的生命。没有这样的记录,浩劫会被遗忘。
此时人们看到的是夷为废墟的城市,而我看向自己的内心。
 (资料图)
(资料图)
在我心里有一个抽象的国家,有座失去昔日辉煌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此刻,我祈愿它远离灾难,远离哀恸。
海鸥飞翔,碧波荡漾,海风劲吹,风光旖旎。
这是2015年我看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的景象。从北京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是7050公里,从首都国际机场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行10个小时,中途在迪拜停留换乘飞机再飞行3个小时才能降落到这片国土。意识到这些你就会格外留心所看见的,体察你所感受到的。比如那些蹲坐在钢架桥梁人行道的垂钓者,他们戴着遮阳帽,望着桥下河流垂钓的渔线一动不动,他们脚边的鱼篓里放着钓上来的鱼,这些垂钓者与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的祝祷者一样,带给我新异感,与蓝色清真寺里的唱诵者一样,令我好奇。
博斯普鲁斯大桥和从它的桥身之下流过的海峡,我在空中就看到过它奔流的姿影,飞机在伊斯坦布尔上空下降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狭长海域。穿越气流和云层缓慢下降,机翼之下是深邃的蓝色,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仿佛是为了玩转奇效,飞机在下降的过程变换着飞行角度,时而倾斜下降,时而平行移动,湛蓝的海洋变幻着不同的形状和姿影,时而如纤细的衣带,时而如铺展的绸缎,最后撞入视野的是湛蓝浩瀚深邃的海洋,矗立在海洋两侧形貌奇崛的俪雅之城。
只有踏上伊斯坦布尔的土地,才能看见这座城市独有的辉煌的遗迹,见识它作为昔日帝国的残败与荒凉。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洲与亚洲分隔开来。在海峡西岸,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又被金角湾分成南边的老城和北部的新城。苏丹艾哈麦德区位于历史半岛区的尖端,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遗产地的中心。乘坐轮渡行进于这世界最著名的海峡之间,我觉得是浸润在异邦的历史和时间之中,也浸润在奥斯曼帝国极盛的繁华与如今的凋零与伤逝之间。
当我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瞬间如见心仪之爱。昔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处都是狭长划艇穿梭往来的身影,它们的船桨有韵律地击打着水流,将苏丹及其侍臣从宫殿载往行宫,从欧洲载到亚洲。现在划艇不见踪影,代替的是伊斯坦布尔的人们喜欢的公共轮渡和快艇。作为土耳其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北连黑海,南连马尔马拉海和地中海,全长30公里,这条海峡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唯一通道,亚欧两岸的山地有着华丽的王宫和辉煌的圣殿,有尖顶教堂,有穹形清真寺。也有造型奇崛的别墅群和朴实而简约的乡间居所,它们都隐没在茂盛的山地丛林中。乘坐邮轮游览托普卡帕宫,在其南麓近距离看博斯普鲁斯海峡,触摸它吹袭而来的海风,铭记它清澈碧波荡漾的姿影。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在前往土耳其的旅途中,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我随身携带的书籍,它跟护照、衣物、银行卡、药品一起成为我的旅行必须携带的物品。“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何佩桦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必然有一位可以传承国家精神,书写城市灵魂的作家。
乔伊斯属于爱尔兰、卡夫卡属于布拉格、佩索阿属于里斯本,帕慕克则属于伊斯坦布尔。
在我入住的酒店大堂里环绕着廊柱的展示台就摆放着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英译本,而我不远万里来到土耳其,抵达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访问帕慕克。在见到他之前,我穿行在伊斯坦布尔老城,流连于旧街,其实也是在寻访体察帕慕克的踪迹,我知道他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他经常跟随母亲乘坐轮渡出海,他养成习惯在居所的阳台上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轮船。在居所的阳台上,帕慕克看见过沉船的海难,看见过邮轮起火,冲天的烈焰焚烧了邮轮,也看见过苏联的军舰列阵驶过。
“博斯普鲁斯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和我的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善良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帕慕克在追忆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
1960年代中期,帕慕克还在就读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其时他花了不少时间站在从贝希克塔斯(Begiktag)到萨瑞伊尔(Samyer)的公共汽车的拥挤走道上,眺望亚洲那岸的山丘,看着如神秘之海熠熠闪耀的博斯普鲁斯随日出变幻的颜色。“一个以城市的废墟与忧伤为题的作家,永远意识到幽灵般的光投射在他的生命之上,沉浸于城市与博斯普鲁斯之美,就等于想起自己的悲惨生活和往昔的风光两者相距甚远。”帕慕克如是写道。
我想,也许地震会摧毁城市的楼群,然而杰出作家构建和创造的世界却恒久。
这是记忆与书写的力量,是文学与艺术的力量。
也是人类文明的力量。
在抵达土耳其之前,我为重新供职的《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约过著名摄影家阿拉·古勒(Ara Güler,1928年8月16日-2018年10月17日)的摄影作品。这位亚美尼亚裔的土耳其摄影师被称为伊斯坦布尔之眼,他拍摄过20世纪最优秀的创作者的肖像,从毕加索到希区柯克。他也是帕慕克的御用摄影师,1994年夏天,阿尔·古勒为《世界报》副刊封面拍摄了作家的肖像。这一年帕慕克42岁,他追忆道:“被阿拉·古勒拍照,让我感到自己将作为作家载入史册不被遗忘。”从1936年开始,阿拉·古勒用一种带有独特的“呼愁”的照片,记录保存着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历史。雾霾笼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停泊在海洋中的陈旧的邮轮,夕阳映照的清真寺、雪幕中的危楼、街巷里劳作中的工人,荒凉的城市废墟、幽暗凌乱垃圾遍布的街道……“看着阿拉·古勒的照片时,城市、街道、风景向我们传递的一些基本情感——忧伤、疲惫、卑微、谨慎——通常也会出现在它们面前的人或者人们的表情里。”帕慕克回忆对老友的记忆时写道。
《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阿拉·古勒 摄影[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序 邓金明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通过帕慕克的出版经纪人,获得阿拉·古勒的授权,杂志刊发了伊斯坦布尔专辑。
连帧的黑白照片令人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使我更真切地感知伊斯坦布尔。
2019年9月26日18时59分,伊斯坦布尔有过一次震级为5.7级地震。清真寺的尖顶被震断,470座建筑物受损,14所学校的建筑物出现裂痕。此时摄影师阿拉·古勒已辞世,然而我依然看到陷于地震恐慌的伊斯坦布尔,我已知土耳其是地震带的国家,地震是土耳其最为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它的96%的领土位于地震带,属于全球地震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更早的时间(1998年)我编辑过一部图文书《目击世界一百年》,看到过土耳其大地震的纪实摄影,破碎的城市,哀恸的人,这些镜头令我过目难忘。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的地震让我想到伊斯坦布尔之旅。
我是怀着犹疑进入土耳其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飞机驶往土耳其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中途在迪拜转机,候机楼的蓝色橡胶座椅坐着戴着头巾、穿着罩袍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机场的广播响着穆斯林的呼拜声,这一切已经让我看到它的异质性。
真正抵达伊斯坦布尔,在汽车淤积的公路听着司机暴躁地跟人吵架,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在车流中闪过,在尘土飞扬的街巷里穿行,夕阳西下映照着清真寺的轮廓。
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海岸时,我感觉自己如同沙粒飘落沙岸。
栖落的鸽子密集而悠闲地在海边的公共广场觅食,它们时而振翅飞起,时而降落,在人的脚前活动,轻松而自在,显示着伊斯坦布尔的鸟类与人类友好共处的温馨感。
阳光照耀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海水清澈如宝石绿,快艇在海面驶过划出白色的浪影。对岸隆起在林木之间的亭台楼榭可见帕慕克笔下的雅俪别墅。
现代人不需要置身灾难的现场,也可以认识灾难。除了地震,还有飓风。我真正认识飓风是在好莱坞电影《星际穿越》,美国南部乡村,这是从天空降下的灾难,飓风袭来时漫天的黄沙在气旋的裹挟中狂暴地袭击着村庄,这部电影让我们认识了飓风的威力和它制造的灾难,也让我知道诗人狄兰·托马斯以及他的著名诗句:“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还有从大海袭来的灾难,海啸。2015年春天,我有机会乘坐哥斯达号海上邮轮,沿着香港起航,驶往日本冲绳列岛。这是在太平洋的航行,由此真正见识大海的力量,感受到海洋的狂暴。
然而,跟那些狂暴的灾难与浩劫比,我当然更迷恋人类的安详与宁静的时刻。
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酒店外的老街意外地感觉美好。
海鸥、鸽子和麻雀,这些类别不同的鸟就在窗外的楼群之间或展翅飞翔,或落地嬉戏。街上不时看到慵懒着走过的猫狗。街巷安静,人们多在睡梦之中。我会独自走出酒店沿着老街走,到临街的塔克西姆广场散步,观看老城的街景和人群。尽管上街就能看见伊斯坦布尔的混乱与残败,可是我也能体察到它的寂静和安谧。
伊斯坦布尔在它的城市史中有过不同的名称,比如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它曾经是土耳其历史上历代帝国的首都,作为奥斯曼时代遗留下的城市遗迹,它记载了曾经由极盛时代的辉煌转向衰落时光。世事已如烟海飘逝,而历史也已化为尘埃,我们能面对的就是它的遗迹。
到伊斯坦布尔除了它的城市风貌,它所拥有的自然与历史遗迹是必须要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宫、蓝色清真寺,这都是我想要体验的场域。踏上土耳其的国土以前就知道圣索菲亚教堂的影像,了解它在世界宗教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显赫声名。
有机会亲眼见识它的辉煌文明的遗迹,这是我安享的收获。
2023年2月6日的土耳其大地震,让我想到2008年的中国汶川大地震。
在地震的灾难中,人类的境遇和状况是相似的。我记得当时的震撼和哀恸,想要亲历灾难的冲动使我踏上前往汶川的旅途。记得那时编辑想要拿到帕慕克的稿子,报纸想要呈现大地震的人类命运。每到灾难发生时,人们都会寻找作家,似乎他们的目击、亲历、体察和表达更值得信赖。同住地球之上,对于大地震的经历和认识,无论东西方都是相似的。尽管我们的国度不同,生存所依靠的语言相异。我们需要借助文学的艺术和深度展现浩劫带给人的影响,需要通过杰出作家的思想安抚重创带给人的哀恸。其时我当然知道帕慕克,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知道。他的《新生活》《黑的书》《雪》,都是我的案头书籍。
通过我熟悉的出版公司联系到帕慕克的经纪人,获得帕慕克的授权发表他写土耳其大地震的文稿。报纸刊出帕慕克写土耳其大地震的文章时,我已到达地震现场。城市公园,体育场,只要有空地,遍布人群浩大的避难者。运送震灾伤者的直升机日夜轰鸣,升起或降落,盘旋在成都的上空;医院的伤残者人满为患,到处是呻吟之声;街头的广告栏贴满寻人启事,在震灾中失踪者已难觅形影。前往震灾之地时,沿途可见山体崩塌,公路断裂,楼群粉碎。
我踩着废墟中的瓦砾,勘察受难者的遗迹,也寻找幸存者的踪影。
灾难与哀恸,是连接我们生命的元素。
它可以让生活在异域的人们心灵相通。
“人类居住的并不是宇宙中心,而是一个渺小脆弱的角落。地球漂流在永恒无垠的宇宙之海中,地球之外还有上千亿行星,数十万亿恒星系。”看电视片《宇宙》,20世纪杰出的天文学家卡尔·摩根写道:“从太空望向地球时,国境线并不明显。在群星的城垒之间,我们的星球只是一弯脆弱的蓝色星月。”
人类的生活具有天然的悲剧性。生活在地球之上,必然经历诸多的灾难,地震、海啸、飓风,只要地壳在律动,灾难就不会缺席,它伴随人类的生活。
灾难与记忆,浩劫与体验,这是人类生活的双面体。也因此作家与灾难,作家与同胞,文学艺术与人类的哀恸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它们构成星球文明的星系。
虚构与非虚构,想象性文学,以及科幻(艺术)的发展,因应人类的生活。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T.S.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笛福《瘟疫之年》与《鲁滨逊漂流记》,阿尔贝·加缪的《鼠疫》,都是对灾难的记忆和书写。
在瘟疫猖獗流行的2022年,我看到帕慕克最新的长篇小说《瘟疫之夜》。或许弥漫全球的瘟疫体验使他重述记忆中的瘟疫。
灾难发生时,必有记忆;毁灭发生时,也有幸存者诞生。
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躲过战火,躲过冲突烈焰,也躲过宗教纷争的幸存之物。
当我看到恢弘建筑的轮廓,直觉内心被震撼。湛蓝的天空之下,巨大的圆顶,高耸的石柱,矗立的宣礼塔,厚重的砖石砌成的城堡令人震撼。在烈日之下,跟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入前庭院,脚下是长方形石条垒砌的石径,那些粗粝的石头浸透风雨的侵蚀,如同斑驳的古堡砖墙显示出时间流逝的印痕。
圣索菲亚大教堂见证了政教与世俗力量的相互崛起、彼此争夺和最后的征服。教堂现在矗立的位置曾经有两座被暴乱摧毁的教堂,公元532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第三座教堂。在1519年被塞维亚主教座堂取代前,有一千多年,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大教堂易为清真寺。1935年2月1日,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这座见证多个帝国兴盛衰亡的建筑对世人开放。
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杰出艺术的集合,精湛技艺的珍存。
皇室之门,是进入教堂穹形大厅的必经之道。出现在正面穹形顶壁上的是左右两幅奥斯曼大勋章,在勋章的上方是一幅镶嵌画,它描绘了“万物的主宰耶稣”的肖像,穿过这扇门就是建筑的主空间,它以圆顶、巨大中殿和金色镶嵌画而著称。这个空间的重点是壁龛和华丽的镶嵌画,我看到那幅著名的《圣母和圣婴》的画像,这幅镶嵌画创作于九世纪。壁龛上方的镶嵌画曾经描绘天使加百利和米迦勒,现在只剩下不完整的片段。历任拜占庭国王都是在圣索菲亚教堂加冕的,加冕时王座放置在正厅里那块装饰着一圈圆形大理石的登基方石中心。
圣索菲亚教堂的二楼是镶嵌画的画廊。从内部前厅北端走上一段回转的斜坡即可进入画廊。这是由大小不等的卵石铺砌起来的坡道,长久被人踩踏,卵石被磨出光泽。穿过曲折回旋的坡道上到二楼,这是皇后观礼的位置,一个由绿色大理石铺就的大圈标识出皇后座位的方位。二楼的画廊保存了多幅镶嵌画,其中有一幅名为《最后的审判》(Deesis)的残余部分,这幅创作于13世纪的镶嵌画绘有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在一起的肖像。
美丽之门是教堂必经的通道,这是一座铸造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宏伟青铜之门。走出“美丽之门”,放眼回望教堂,重新打量这座气势恢弘,结构繁复的圣殿。圣索菲亚教堂以其创造性的建筑形式、丰富的历史内涵、宗教价值以及非凡的艺术之美成为伟大的历史遗迹,置身这辉煌圣殿中,惟有惊叹人类杰出的创造和构建能力。
是这杰出能力创生出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
无论遭遇怎样的浩劫,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幸存者,见证,也记录。
此刻,我想这美丽之门依然敞开,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存在。
我的伊斯坦布尔。在2023年2月6日,袭击土耳其的浩劫中——
不在场。使它躲过灾难,成为幸存之地。(本版图片摄影:夏榆)
作者:夏榆
流程编辑:u008
关键词: